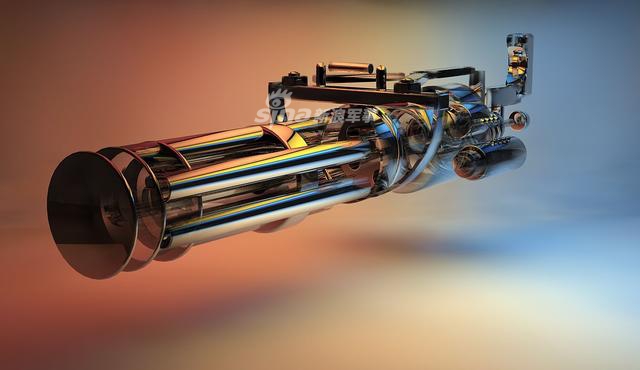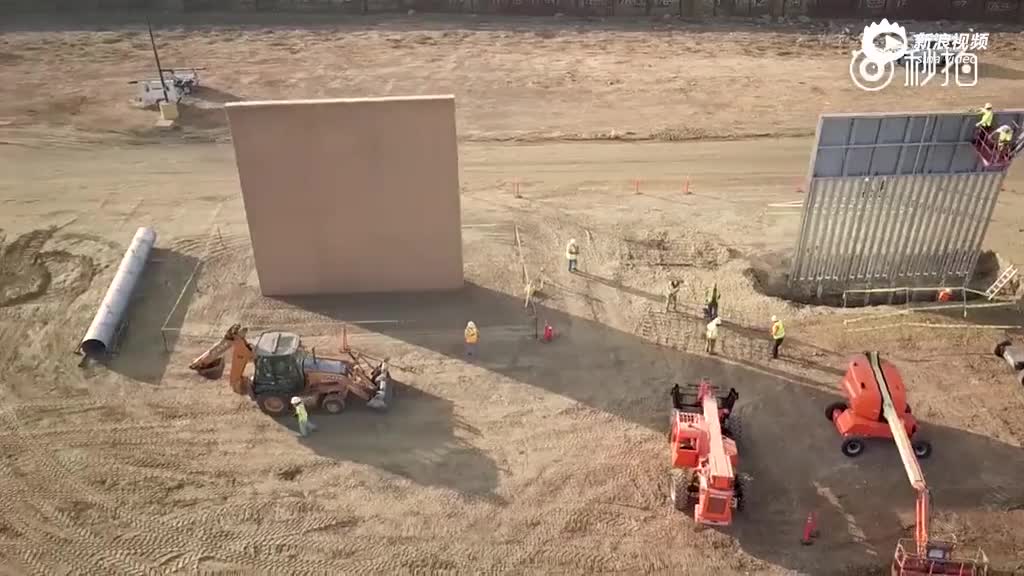文学副刊评论区留言,将综合留言质量和热度,每月评选2位读者,分别赠送名家作品集2册。
阅读是一种心灵的享受。一起阅读,让文学温润的光照亮心灵。

缘来缘去缘如是
作者:陈庆伟
人生如寄,逝者如斯。谨以此文缅怀业已先我而去的亲朋故交。逝者为尊,排名不分先后。
——题记
小昌论辈份,小昌是我侄子,没出五服。也就是说,我要是有什么事,或者碰到什么困难,即便不求助,他都会在第一时间主动帮我。
小昌学名叫玉昌,按祖上谱系,应是毓昌,钟灵毓秀的毓,繁荣昌盛的昌,饶有古风。可惜族人虽以耕读传家,诗书继世为家训,终是善耕的多,好读的少,加之毓字比较生僻难认,便易毓为玉了,对此,我深感惋惜。在一切尚简的时代,我们抛弃了太多美好的东西。

按家乡风俗,我一直称呼他为小昌。小昌是家里的长子,因不喜读书,早早辍了学,专事汽车维修之类的行业,既有一技傍身,又缓解了家庭压力。农村的孩子能吃苦,要强,再加上一些特有的禀赋和机缘,他在本地汽车维修行业竟闯出一片天地来。巅峰时期,他竟在县城繁华地带开了一家汽修厂,俨然一幅乡镇企业家气派。我最后一次见他时,他还酝酿着要买奔驰或林肯牌的私家车,并为不知如何抉择品牌而纠结。可惜不久后就听到他喝药自尽的消息,令人唏嘘。
我离家较早,除了血缘维系之外,与小昌原没有太多情感交集。倒是前些年网络刚盛行时,我在网上建了一个叫陈门口的贴吧,并随手发一些乱七八糟不知所谓的东西。陈门口是我老家的村名,小昌常上去发贴,但多以逗我为主,并没有什么主题。后来贴吧被铺天盖地的广告占领逐渐荒疏,我也没了打理的心情。倒是偶尔回乡见到小昌,他总是笑吟吟地问,二叔,陈门口吧该锄草了——锄草就是清理广告的意思。打趣的同时,他还向我了解广东汽车行业发展情况,还有广东的天气美食之类,说要到广州找我玩。我只当他在说笑,也没有放在心上。
没想到他竟真的来了。有一天突然接到小昌电话,说要来广州考察一下二手汽车市场,顺便过来看我。我很高兴,没时间去机场接站,就把详细的乘车路线编了条短信发他。原以为他会埋怨我,没曾想他见到我竟高兴的像个孩子,夸赞我短信编的详细,哪里上车哪里转车哪里拐弯都非常详细,很容易就找到了家。因好久不见,他有些含羞的样子。当天我把自己的床让给他,带妻子和儿子挤在一起。第二天又陪他到广州的几个二手汽车市场调研,彼时汽车价格已经透明,沿海和内地行情差别不大,他有些失落和懊恼。临别时我请他吃饭,他竟趁我不注意把账结了。唉!

我一直以为小昌读书不多,不会有太复杂的思想和情感。事实并非如此,他不仅感情丰富,而且懂得感恩。我每次回老家,他都郑重其事地请我吃饭。每每提及广州接待他的事,总是感慨:二叔对我真好啊,把自己的床都让给我睡。
老家的风俗,男孩子一般结婚都比较早,二十岁左右就结婚的很多。小昌也是,若不出意外,他四十多岁就可以作爷爷,过上四世同堂的幸福日子。或许结婚太早的缘故,抑或初恋时不懂爱情,总之,他夫妻二人并没有人们想象的幸福,加之小昌内向的性格,矛盾终于升级并最终以一种决绝的方式惨烈爆发——有天晚上,小昌携了一瓶农药跑到附近山上喝下,给家里打了最后一个电话:我服毒了,在山上。
亲人们疯了一样,找了一个晚上,无果。或是父子缘份未尽,第二天一早,他七十多岁的父亲最先发现了他,老泪纵横……
这世上,许多事原本就没有对错,更何况爱情。夫妻之间,要么包容,要么忍让,甚至可以选择远离,为什么要以这种不堪的方式选择逃避呢?
钟灵毓秀的毓,繁荣昌盛的昌,多好的名字,真可惜!
四哥四嫂四哥四嫂是一对薄命人。四哥是教师,犹记得当年一本类似于县志名录的书,市优秀人民教师的名单上就有他,我一度引以为傲。四嫂小家碧玉,大眼睛,两条及腰长辫,清纯,美好。俩人平时相敬如宾,举案齐眉,再加上有儿有女,还有四哥光荣的人民教师称谓,很让人羡慕。

四哥做过我们村办小学的校长,彼时我刚入学,便十分喜欢听他讲话。他的声音非常好听,慢条斯理,抑扬顿挫,举足投足,师者风范。四哥因病动过手术,脖梗上有一道长长的伤疤,每当讲话的时候,高耸的喉结都会配合着那道伤疤上下浮动,在我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有时非常严厉,记得我在学校捡到一个粉笔头,在墙上一边走一边划,恰好被四哥看到,我以为他会像在家里一样和我打个招呼,抑或开个玩笑,没想到他一脸严肃,狠狠批评了我。我心里很难受,这是我的四哥么?
当然,在家里的时候,四哥对我们很和霭,他高兴的时,喜欢让儿子小勇骑在他的肩膀上,我也经常和他开一些没大没小的玩笑,他从不生气。虽是兄弟,四哥老师的职业习惯却一直改不了。他一直把我当作一个小孩子,每次见到我都要问同一个问题:小明割了一斤草,小花也割了一斤草,两个人一共割了几斤草?我假装考虑半天告诉他,两斤草。他听了很高兴,好好好,书没有白读,继续努力。我也很高兴。其实我算术并不好,每次考试成绩都很差,但在四哥面前我却充满自信。在他眼里,我不仅是一个孩子,更是一个学生,而这个永远一加一等于二的游戏,不过是他作为兄长或教师表达个人情感的一种方式而已。
四哥的毛笔字写的很好,或许家传,又或许是作为一名教师必须掌握的素质。他的毛笔字以正楷为主,有盛唐气象,董褚之风,每学期结束,孩子们笑吟吟捧回家的奖状,大都出自四哥之手。就在前几年我回老家,还在二叔家里看到一幅四哥写于八十年代的奖状,真是感慨时光的无情和岁月的变迁。
记得有一次我请四哥在《语文》书上帮我写名字,以后许多年,我的名字都是临摹四哥的写法,至今受益良多。当然,那时候的对联,对四哥来说不过信手拈来,不必细述。

后来四哥到乡中学履职,还一度升任乡镇教育部门的主要领导,如果不是后面的变故,我想他的前景应该是极好的。那时候学校组织到乡里考试,四哥请我们几个孩子吃饭,一大筐的肉包子。四哥不八卦我们的成绩,什么也不说,微笑着看我们吃。
四哥恤贫惜老,喜欢帮助人。那时候每个家庭都不富裕,四哥是教师,生活相对有保障一些。左邻右舍谁家有困难,他总是乐于伸出援助之手,有时候甚至偷偷瞒着四嫂。他们离开的那一天,许多借了四哥钱的,有主动还的,也有不还的。那时候的人都穷,加之受教育程度不同,生活背景差异大,对事物的理解也不一样,相信四哥也不会怪他们。
四哥四嫂悲剧的那天是个秋天,据说两人拌嘴,本来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吵着吵着就赌气似的找药来喝了,喝之后就后悔了,喊隔壁的三叔拉着板车往乡医院送。四哥走到半路就不行了。四嫂在医院抢救了一天,随后而去。
后来我看梁祝的故事,每当看到成双成对的蝴蝶,我就想,这要是四哥四嫂,该多么好。
中振中振是我中学时期的同学,俗话说的好,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就像现在的一线明星绝对不会和横店的群众演员成为好朋友一样。如果从我们班的成绩单后面往前看,不出十个人就能够看到我们俩。
那时候真是年少轻狂,幸福时光。我和中振经常畅想今后的美好生活。他常说,我要生四个孩子,且全是男孩,名字就从“勇猛刚强”一字排开——说时,他满脸得意,满脸的春青痘都闪烁出幸福的光芒。中振姓张,家里兄弟几个,他最小,且家里没女孩,也许尝到了男孩带来的家族上的荣耀,他有些重男轻女的思想,小小年龄就喜欢胡思乱想。
高晓松曾说,七八十年代的男孩子有尚武精神,那时候男生的偶像多是李小龙,每个人年少时都有一个英雄梦武侠梦,个个都想成为武林高手或者是岳飞文天祥式的民族英雄。中振也一样,特喜欢舞刀弄棒。那时没什么兴趣班,否则的话,他能够成为李小龙式的人物也未可知。有朋友模仿武侠片的样子做了一把“峨眉刺”送我,我知道中振尚武,转手送给了他。他高兴的不得了。宝剑赠英雄,他欢喜,我也高兴。

中学毕业时,彼此还十分伤感,不知道此一别何时再相见。谁承想没过多久,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我到一家技校读书,报到之初,正愁无人一块玩,竟然在教室门口碰到垂头丧气的中振。我学财会,他学建筑,隔离教室,于是我们又一起谈人生,聊武侠,活在当下,畅想未来,快意恩仇。
后来,我偶尔通过县里面的邮局给他写信,无病呻吟地说一些闲话。有时候写得太多,担心信件超重,我还特意贴两张邮票。他就回信骂我,你个败家子,贴那么多邮票干什么,真是浪费。话犹在耳,物是人非。
九十年代末,我们一起去当了兵,不过一南一北,但通信未断,彼此说一些军旅话题。他是舟桥兵,经常给我讲武装泅渡之类我不大感兴趣的话题。再后来,好长时间没有他的消息,有一天意外收到一封他哥哥寄来的信件,才突然晓得中振新兵下连时,因车辆事故不幸牺牲了。
一时间我呆若木鸡,脑袋全是那个长满青春痘的武侠少年。
我姨我姨是我妈的亲妹妹,她俩还有个哥哥。据说舅舅和外公关系不太好,一气之下出走东北,多少年音讯全无,甚至在外公去世时都没回来。
所以说,我姨是除了外公之外,我母亲娘家人中唯一的一个亲人。甚至亲到两个人要嫁到同一个村子来。有趣的是,姨父和我父亲同宗但低一个辈份,在称呼上,姨父呼我父亲为大叔,我姨呼我父亲为姐夫。我和两个表哥之间,如果按父辈份是叔侄,按母辈论是兄弟,真是有趣。我母亲和姨还有一个共同的媒人,就是先她们之前嫁到我们村的,母亲和我姨都叫她姐姐,而我叫她二奶奶的。他们三个人都姓薛,看来这三位“薛姨妈”和我们村是有缘分的。
中国的姓氏是个伟大的发明,据说从科学的角度讲,男性的什么染色体或者是基因之类的,经过几百上千年岁月流失,都能够从中找到共同的生命密码,比如前些年曹操墓发掘过程中出现的寻找曹氏后人从中证明曹操身份的故事。也因此,中国的孩子和姑妈亲的比较多,姨妈似乎远了一层,总感觉莫名的隔阂。对此我感同深受,在姑妈家可以无拘无束,在姨妈身边,似乎总抹不掉亲戚的概念。每次母亲带我到我姨家做客,我总是闹着要赶快回去,虽然姨妈对我也是疼爱有加。

有一年母亲和我姨都还健在,她们带我到外公家做客。表哥准备了很丰富的午餐。席间姨妈有些反常,两眼直瞪瞪的,拿着馒头,一边吃一边念叨,哎呀,好久没有吃过这样好吃的白面馒头了,真香啊,等等一些我听不懂的话。我感到十分纳闷,每天都吃白面馒头啊,怎么说出这样摸不着头脑的话来。母亲有着丰富的生活经验,赶忙走到姨妈背后,用两手按住她的双眼使劲往里抠,一边说些我依旧听不懂的话。不一会儿,姨妈长叹一声,恢复了正常状态,问她刚才说了什么,她竟然什么也不知道。
后来我听母亲说,是过世的外婆附上姨妈的体,借姨妈之口说话。外婆经历过灾年,因饥饿而死,所以看到白面馒头有此感概。我是坚定的唯物主义者,但对于那天发生的事,我始终没有找到一个令自己信服的理由——两个没有任何利益纠纷的亲姐妹,完全没有必要在一个孩子面前表演这样无聊的游戏。
姨妈深受疾病之苦,走的时候不到五十岁。那两个和我既是叔侄却又是兄弟的表哥,均事业有成,在各自领域都有一番建树,成了我学习追赶的榜样。如果我姨泉下有知,也一定会开心的笑出声来。
二叔二叔去世的时候不到五十岁,彼时大堂哥正在备战紧张的高考,堂哥堂姐也在读书,二叔是家里的顶梁柱,就那样哗啦一声,顶梁柱塌了。
二叔那一辈人,经历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系列的苦难,缺吃少穿,孩子多,不要说读书识字,能够侥幸活下来不被饿死就十分幸运了。或许爷爷比较开明,我的父亲和叔叔们都还识得几个字,特别是二叔,读书不多,凭着自己的聪明,竟然还当过生产队的队长或财务之类的职务,十分不易。

后来生活条件好了,二叔贪玩,或者说,热爱生活。他和村里面几个青壮年一起,用很细的绿纱窗做了一张大概十几米长的拉网,到周边各村池塘去网鱼。彼时青山绿水,没有环境污染,农村也没有养殖的习惯,各村都有几口池塘或灌溉用的小河,里面很多野生鱼。他们带我一起去,二叔骑着一辆老款二八式自行车,后面载着渔具,我坐在前面横梁上,一路上硌的屁股生疼,却感到非常快乐。附近村子随便转,池塘的鱼随便抓,一上午就可以装上几十斤,回来按人头分配。我跟着二叔玩的,也有一份,真是开心。
二叔的病本来可以及早发现的,有症状的时候他没在意,也许是舍不得花钱的缘故,一直硬顶着,等到实在顶不住的时候才去医院,已经是晚期了,手术后在家偏瘫。我偶尔过去看他,他就问我,我的病能好么?我说没事没事,锻炼锻炼就好了。他就很开心,或许早已预知某个结果,依然对生活充满依恋,每天架个拐杖,在院子里踱来踱去,消磨自己最后的时光。
堂哥大学录取通知书下来的时候,二叔已经昏迷不醒了。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堂哥能够考上大学。堂哥拿着录取通知书向他报喜的时候,他没有一点反应,我想他应该感受到了。
姑姑们说,二叔年轻的时候头脑灵活,爱动脑子,不墨守成规,不愿屈服于命运安排。那时候的二叔凭着自己的聪明,从外面弄来不少吃的,为家里解决了很大的现实难题。父亲和姑姑们就是吃着二叔弄来的食物才缓解了饥馑之苦。二叔是家里的一个功臣,姑姑们说这番话的时候,眼里都眨着泪花。
人生就像一个长长的锁链,一环连着一环,每一环都是一个人,排着队,向前方一个叫做未知的地方延伸过去,然后在属于自己的年轮里刻划出一条属于自己的人生轨迹。有的人生轨迹漫长,有的人生戛然而止。我经常想起一起一些人,假设他们如果还在,应该是个什么样子。想起他们,回望已逝的岁月,才会更加珍惜当下。因为,我们和他们一样,都是普普通通的平凡人。也希望,在若干年之后,也会有人像我想起他们一样想起我。
本文图片来自网络。

陈庆伟,业余文学爱好者,现居广州。散文、杂文见诸《青少年书法杂志》《青少年书法报》《济宁日报》等报刊杂志。散文《站在中轴线上》曾获广州诗社举办的“迎亚运诗词散文大赛”散文组优秀奖。出版内部交流散文集《疯话薛曰》。

更多猛料!欢迎扫描左方二维码关注新浪军事官方微信(sinamilnews)
推荐新闻
- 【 新闻 】 刚宣布驱逐俄外交官 6国又要抵制世界...
- 【 军事 】 辽宁舰携40战舰现南海 美呼难以置信
- 【 财经 】 中美贸易逆差从何来?美国真吃亏了吗...
- 【 体育 】 C罗连夺葡萄牙足球先生 穆帅亦获奖
- 【 娱乐 】 张继科公开认爱景甜 海边牵手超甜蜜
- 【 科技 】 独家专访库克:如何给iPad添加教育属...
- 【 教育 】 担心男生太娘 浙江一中学推阳刚体育课
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电话:010-62675637
举报邮箱:jubao@vip.sina.com
Copyright © 1996-2017 SINA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新浪公司 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