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师追忆国庆阅兵:为拍苏-27造成听力受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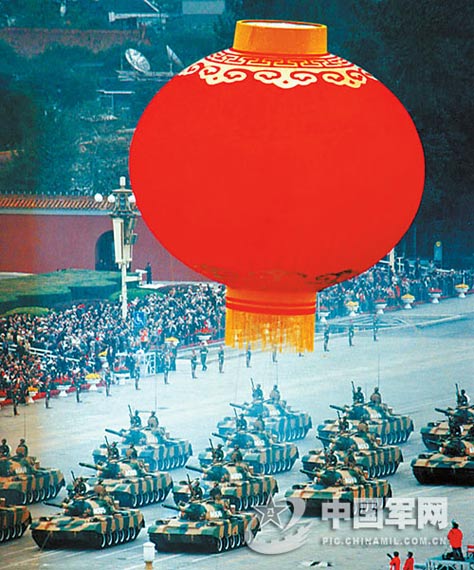
王 瑜 秦培栋
题 记
无论显赫或卑微,每个人都在历史的长河中,用生命的痕迹记忆着过去,哪怕是一横一竖,一撇一捺。与其他人有所不同的是,那些用手中镜头记录一段段难忘历史的军旅摄影师们,在尊重历史的原汁原味时,也融入了更多个性化的情感和行为方式——他们创造了历史,却浑然不知,他们定格了历史,却不以为然。他们只知道,作为军人,命令下来的那一刻,就是抱起手中的“武器”,冲啊!
张世鸿:用彩色胶片拍摄阅兵第一人
他板直的坐姿让人感到一位老军人的风骨。即便身体已被岁月的沧桑浸染,但透过他的话语,仍能体味到军旅摄影家不变的爱国情怀。眼前的他参加过抗美援朝,曾在战火硝烟的前线穿梭拍摄,将后勤保障战线的大批摄影资料送到后方。他还接受过秘密任务,进入某地连续工作了701天……
都说他的镜头弥足珍贵,记录下了新中国成立来无数关键的历史时刻。他就是张世鸿。
与他面对面相坐时,周围的人都亲切称他张总。因为他是八一厂许多电影和纪录片的总摄影。
他今年70多岁了,但身子骨出奇的硬朗。他拍着胸脯笑着说:“这是常年扛着笨重的摄影机,走南闯北锻炼出来的军人体魄。”直到现在,张世鸿还是不服老,想着跟腾安庆(1999年《世纪大阅兵》总导演)比拍黑白片,看谁拍出来的镜头最棒。
追忆是从1956年10月1日的阅兵式开始的。张世鸿说:“八一厂当时正在拍一部关于苏加诺访华的片子,没想到苏加诺也去参加检阅了,我们就跟到阅兵式上去拍。完全是一种巧合。”
“那年的阅兵下着雨,元帅们都换上新授衔的军装,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部队。方队从雨中走过,那齐刷刷的队形,那官兵身上散发出的雾气,特别美,也特别令人神往。”张世鸿回忆起50多年前的场景,就好像刚刚发生过。
“我出发前就想好了,这一神圣时刻要用彩色胶片拍,但是阴天,又有一种担心:用彩色胶片拍下雨的场面,会不会砸锅?因为那个年代谁也没用过彩色胶片,心里没底。当时现场还有其他电影厂的摄制组,他们保守,不敢冒险,就用黑白胶片拍。我天生胆大,决定破天荒使用彩色胶片。我知道这是一次性拍摄,方队走过去了,再想弥补是不可能的。结果拍出来一对比,我兴奋地叫了起来。黑白片拍得雨天灰蒙蒙的,几乎看不清楚,而彩色胶片拍出来的,层次感很强。搞摄影的都知道,头一次用彩色胶片拍大场面,最难掌握的是曝光时间,否则就会一片模糊。没想到,稀里糊涂成功了。”
更让张世鸿想不到的是,10年后,美国出现了“新彩色摄影”理论,一个叫做威廉·埃格尔斯顿的摄影师提出要使用彩色胶片拍摄“严肃题材”,而另外一位萨丽·奥克莱尔的摄影师则认为,彩色胶片在上世纪60年代依旧没有成熟,他的理由是,彩色胶片反映的主题色彩过于夸张,很难把握,弄不好会拙劣地表现世界,无法真正用镜头构建世界。在一片争论声中,“新彩色摄影”理论诞生了,并被归结为是美国摄影师开创了彩色摄影的新时代。
然而,让美国人想不到的是,大洋彼岸的中国八一厂的摄影师们,在上世纪50年代就已经将镜头对准了声势浩大的阅兵式,并将彩色摄影这“难以把握”的主题色彩神奇般地把握住了——在蒙蒙雨中如实并严肃地营造出了一个绝佳的视觉语言和影像效果。如果美国人得知的话,恐怕就不会武断地说是美国摄影师开创了新彩色摄影的时代。
1984年,小有名气的张世鸿,被八一厂作为总摄影,负责拍摄当年《国庆阅兵》纪录片。那时,张世鸿拍摄技术和经验首屈一指,厂领导之所以把这么重的担子压给他,看中的是他的业务。其实,从表象看,张世鸿长得很年轻,怎么看都不像个领导。但张世鸿是一个有激情、有责任心的人,拍摄准备期间,他提出一个主导思想:今天的历史是留给后人看的,面对大阅兵这样的重大而又严肃的历史题材,真实纪录当时的情形就是对历史的尊重,也是对后人负责。因此,他和摄制组同仁讨论再三,最终决定用传统手法纪录阅兵全过程。
他清晰地记得:“阅兵那天,邓小平主席的讲话刚结束,全场就响起雷鸣般的掌声,随之,出现了一点间隙性的平静。伴随一声‘分列式开始’的口令,令人瞩目的受阅部队开始通过天安门——排山倒海的口号声和铿锵有力的脚步声如同大地上滚过的惊雷。由于当时器材落后、笨重,没有同期录音的条件,所以现场声音都要后期加工。我要求每个摄影师凭印象记住阅兵全过程的所有细节,以便事后注入现场声音效果时,严丝合缝。果然,片子制作出来一看,比现场更逼真,更有气势。一位我多年的老战友跟我说:‘我就喜欢听你配的这些声音,真切动人。’”张世鸿说到这里,脸上明显露出了自豪感。他的妻子拍着他的肩膀笑着说:“你这些事有什么值得吹的啊?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一件事就是嫁给了一名新闻纪录片的摄影师!”但从她说话的表情中,能感觉出作为军人妻子的骄傲和自豪。
张世鸿笑了,指着他的妻子对笔者说:“她也不容易,我年轻的时候因为工作需要到处跑,她在家里一个人带孩子。抗美援越的时候,我出去了两年,中间没通信,她都撑过来了。现在年轻人不会理解,两年不通电话不写一封信是什么感觉。”他妻子笑着说:“嫁给搞新闻纪录片的女人不都这样!”看着互相打趣的老两口,笔者感受到了他们之间的温馨和彼此的信任。也只有经历过磨难的感情,才能如此沉静和深邃。
王建国:拍摄《世纪大阅兵》是场战斗
1999年10月1日,是祖国50岁华诞,恰逢世纪大阅兵。全国人民对这一天都充满了期待。
值得欣慰的是,由于中央电视台的现场直播,使亿万观众当天就收看到了阅兵实况。可是,也因为电视转播的局限,许多镜头无法兼顾。正是八一厂拍摄的大型纪录片《世纪大阅兵》,弥补了这一缺憾。
《世纪大阅兵》的总摄影师王建国回忆:“那真是如同一场战斗,每个摄影师都是士兵,时刻经受着考验。那年遇到了腾安庆这样一个好导演是我们摄影人的福气,他很有魄力,很能张罗,既有亲和力,又有聪明的头脑和领导魅力。当时厂里的要求只有一句话:拍摄一部让观众喜欢且震撼的纪录片。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可想而知有多难。为寻找《世纪大阅兵》的创新点,腾导绞尽脑汁地先从纪录片的片头开始寻求变化。他事先领着摄影师们跑遍了北京城,拍下了许多展示国威军威的精彩镜头:故宫的大门在威武的锣鼓声中打开,寓意国门打开,中国人走向世界。还有黄河的壶口瀑布、清华的纳米技术、国防大学的上将和中将们在现代化电教室的沙盘前作业、硕士生和博士生从清华大学的大门一拥而出……尽管有些镜头最终在审查时被拿掉了,但片头还是一改过去从天安门拉开的固定模式。”
对于拍摄中遇到的艰难,王建国更是记忆犹新。他说:“最揪心的是下雨。没想到,9月30日那天真就下起了雨,让所有在场的人心焦不安。据说气象专家们早在一年前就开始对50周年庆典活动当日的天气进行过预测和分析,并准备在必要时人工驱云,但到了那天就是雨下个不停,谁也说不好何时才能多云散去见晴天。制片部门买来了雨衣、雨布,摄影师们带上了‘快片’(一种适宜阴雨天使用的胶片),准备打持久战。冷雨伴着秋的寒意阵阵袭来,冰凉沁骨。摄影组在金水桥等多处设了器材集散点,器材箱下垫一层雨布,上面再盖一层,看守的几个人则穿着雨衣打着伞在雨夜里站着。这一夜,天安门广场的各个方向,都有《世纪大阅兵》摄影组人员在彻夜值班看守机器。”
八一电影制片厂是一支部队,命令一下,所有人就必须到位,每位同志必须保证完成任务。导演部门事先绘制了完整精确的机位图、统筹图,写出了每一台摄影机的分镜头,所有内容都同时有3至6台摄影机做不同景别、不同角度的拍摄。除完成各自的分镜头外,摄影师还根据现场变化,不失时机地抓拍一些精彩内容。王建国说:“按阅兵指挥部的要求,我们的机位由58个一次次递减到最后的29个,机位图也反复画了许多张,每一张都很细致,不厌其烦地标出摄影机和小汽车等实物图像。当机位图拿到阅兵指挥部时,审查者都竖起拇指夸奖:‘到底是八一厂,真是正规、严格!’腾安庆对全厂的摄影师了如指掌,他按照每个人的特长进行了分工,力保每个镜头都尽善尽美。”
“负责拍摄中央领导人讲话的王保权,在阅兵式即将开始前试机时,电瓶突然短路起火,一股白烟腾起,瞬间烧焦的胶皮味弥漫了全场。安保人员怕出危险,索性把他给赶了下来。好在我们事先有预案,下面有专人接应,赶紧给他换个备用电瓶,又给安保人员做了一番工作,才再一次进入现场。当时吓出我一身冷汗,军委主席的讲话差点拍不到了。王保权拍完之后,整个人瘫在地上,也不知道是累的还是吓的。”王建国今天说起这些,仍然心有余悸。
最难办的是一个人跟拍,常常手忙脚乱。王建国记得,当时王迎军扛着摄影机,从纪念碑后面出来,一路小跑跟拍到升旗的地方时,一卷胶片就用完了,他只好跑到军乐团指挥平台旁,将事先隐藏好的另一台机器扛起来继续拍。胶片拍完了,再回来给两个机子同时换片。多次反复,阅兵式快结束时,他已累得端不动机器了,只能趴在地上拍。
王总对他指挥的兵的表现,异常满意,他说:“大家都很卖力啊!董亚春拍摄阅兵村时,一会儿趴在地上,一会儿爬上高台,只为拍出好镜头,顾不得自己的形象。站在历史博物馆顶上的桑华,临场发挥的很出色,他用长镜头把海军在进入东华表之前的7步走,拍得相当漂亮,加之,海军服装是白裤子蓝上衣,飘带随风而动,像波浪滚滚而来。我安排两台摄影机拍摄江主席检阅部队时的一举一动。给我们开红旗轿车的司机叫辛亦农,他的技术很好,为保持车距,他一边要随时盯着驶在前面的中央电视台摄影车,一边还要在反光镜中瞄着江主席的检阅车。他完全专注于自己手中的方向盘,以至于他像是根本没听到检阅部队惊天动地的吼声。”
《世纪大阅兵》纪录片完成了,王建国长长地舒了口气。坐在剪片室的平台前,看着一个个精彩的镜头,他心里乐开了花。他说:“这部纪录片拍出了军人的刚强和气势,也拍出了人民武装力量对党、对祖国、对人民的一片忠诚。不论哪一支方队,不论你横看、竖看、斜看,每一个排面都整齐如一人;每一条头线、胸线、臂线、脚线都笔直如刀割。我从没见过这么整齐的画面!”
如今,《世纪大阅兵》已被视为经典,凡天安门城楼开放时,都在不间断地播放。上到省部级领导,下至青少年学生,无不因它而慷慨激昂。为此,王建国谦虚地说“我也是一个兵,和阅兵村的官兵们一样,自受领了任务,就把自己的全部感情和最佳状态投入进去。如果说,战士的美来自烈日下黝黑的皮肤、双腿上沉重的沙袋,那么,摄影师的美就在于对伟大祖国的忠诚,对这支军队的崇敬,对摄影事业的热爱。”
石少升:与共和国同生同庆
石少升是军事片部的领导,工作很忙。他肤色黝黑,带有北方汉子憨厚的嗓音。他曾参加过1984年和1999年两次国庆阅兵的拍摄,今年还将参加60周年阅兵典礼的拍摄。
石少升1949年出生,是共和国的同龄人。他清楚地记得,1984年的10月1日正好与他35岁的生日重合,那一年他被头一次选中参与国庆阅兵的拍摄。他的位置就在东华表红墙下。当时他属于八一厂的二线摄影师。
“阅兵前,邓小平主席要视察阅兵部队,选择看望装甲兵官兵。当时厂里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我又兴奋又害怕,担心出岔子。进入现场那天,我被安排的位置果然不好,装甲车的炮塔刚好挡住了我的镜头,怎样拍效果都不理想。我灵机一动,就大胆爬到了装甲车的顶部。这在当时是违规的。等安保人员发现驱赶我时,我已抓拍好了。事后我受到了表扬,我抓拍的这组镜头被导演用上了,而且是原封不动。导演给我的评价是,作为摄影师,他总会在临场有让人意想不到的发挥,而这些发挥让整组镜头都显得灵性十足。”
石少升最难忘的还是参加1999年国庆阅兵,他被组织指派去拍摄航空兵部队的演练。他说:“刚去很兴奋,拍摄空中编队,这是我梦寐以求的事。没想到合练开始后,和我的想象完全不一样。他们合练的机会也就那么两三次,合练的机场却有远有近,你刚拍了这里的起飞,得赶紧乘车赶到另一个机场,再拍那里的,来回奔波穿梭。有些镜头我想去拍摄,但是空军配合不了,只能另辟蹊径自己想办法弥补。当时制片主任也很着急,跟我反复商量怎么拍。我给厂里表态,不管难度有多高,一定不折不扣完成任务。”
“经过努力,我终于获得了到空中拍摄的机会。那天,为保证拍摄质量,我被安排坐在飞机前驾驶的位置,驾驶员坐在我后面。大家上飞机前都知道,这样做危险性极大,如果飞机高空停车,那么在我后面的驾驶员就束手无策,我俩只能弃机。但我觉得干什么事都有风险,为了拍摄好镜头,也只能硬着头皮这样干了。”石少升今天回忆起来,依旧不寒而栗。
“飞机降落的时候,也同样危险。驾驶员坐在后驾驶的位置上有视觉差,准确度不够,就会出现偏离。如果偏离过大,很有可能会撞到塔台。当时我坐在飞机上没有感觉到什么,但走下飞机,工作人员告诉我原委后,我只觉得脊梁一阵发凉。”但石少升是一位真性情的男人,在他眼里,军旅摄影师就是一个高风险职业,当祖国需要你的时候,你必须有一种特别的勇气和胆识。
“1999年,空军有了苏-27,导演告诉我,事先必须抢拍一些镜头预备着,等到阅兵式那天,如果出现意外,就都晚了。为此,我决定在跑道上对着飞机正面拍摄。当时,飞行方队不干,认为这样太危险。我苦苦哀求,才勉强答应。拍摄那天,可真叫危险,我的镜头稍微正一点,你就会觉得飞机起飞时直奔你而来,那巨大的冲击力,虽隔着二三十米,依然觉得就在眼前。所以说,摄影师为了一个好的镜头,有时是敢冒生命危险的。”石少升这样感叹道。
苏-27升空时超过80分贝的声波,让石少升的耳朵留下了后遗症——听力受损,耳鸣伴着轻度的耳聋,近距离跟人说话常常听不太清楚。
“有件事我一直很后悔。有一年我去拍演习,看到山洞里的炮弹打出去时,巨大的声音冲击波将战士头顶上的帽子都掀掉了。那天,有个小战士在抬炸药,我正好捕捉到了他,他发现我在拍他,手一滑,炸药掉到了地上。当时很危险,他应该马上离开,没想到他弯腰想去捡,炸药爆炸了,他被送进了医院。现在我一想起来就自责,如果不是我当时拍他,他就不会想着去捡炸药。作为摄影师,有时看到别人受苦却无法帮助,这种心里的痛苦是很难言语的。”石少升这番话,体现了所有摄影师的良知所在。
在采访现场,笔者感到了每个摄影师的时尚,无论是张世鸿那身蓝色的牛仔休闲衫、笔直的咖啡色西裤,还是王建国那顶帅气的黑色遮阳帽,都令人忍俊不禁。他们是自信的,他们如同航海的舵手,从容不迫地把重达几十公斤的摄影机当作武器,去记录世间的沧桑,去表达自己的情感。他们洒脱自信,他们坚毅刚强。(本文照片由作者提供)
相关链接:
1、1953年,《人民心一条》获文化部优秀纪录片奖二等奖
2、1955年,《在帕米尔高原上》获文化部优秀纪录片奖二等奖
3、1963年,《伟大的战士——雷锋》获总政治部优秀纪录片奖
4、1977年,《硬骨头六连战旗红》获优秀军事教育片奖
5、1981年,《钢铁长城》获中国电影金鸡纪录片特别奖、文化部优秀纪录片奖
6、1984年,《国庆阅兵》获解放军文艺奖、文化部优秀纪录片奖
7、1992年,《天界》获广电部最佳新闻纪录片奖、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新闻纪录片奖
8、1995年,《较量——抗美援朝战争实录》获“五个一工程”入选作品、中国电影金鸡纪录片特别奖、广电部优秀纪录片奖
9、1998年,《挥师三江》获中国电影金鸡评委会特别奖、“五个一工程”入选作品
10、1999年,《东方巨响》获中国电影金鸡最佳新闻纪录片奖、广电部优秀纪录片奖
11、1999年,《世纪大阅兵》获解放军文艺奖、“五个一工程”入选作品、广电部优秀影片特别奖
12、2005年,《东方神舟》获“华表奖”优秀纪录片奖提名、“金鸡奖”最佳纪录片奖提名
13、2006年,《帕米尔之恋》获第17届意大利“军队与人民”国际军事电影节最高奖“共和国总统奖”
14、2007年,《不能忘却的长征》获“华表奖”优秀纪录片奖提名、“金鸡奖”最佳纪录片奖提名
15、2008年,《为了生命》获第19届“军队与人民”国际军事电影节社会影响类一等奖
(崔 腾辑)
更多关于 阅兵 的新闻
- 国庆60周年大阅兵陆航编队将更复杂更有气势 2009-08-11 14:19
- 解放军兵工专家称最新武器将亮相国庆阅兵式 2009-08-08 09:54
- 中国将以更先进火箭技术产品参加国庆阅兵 2009-08-05 18:27
- 国庆50周年阅兵参阅女民兵秀发被军博收藏(图) 2009-08-04 12:00
- 空中预警机新型远程火箭炮可能亮相国庆阅兵 2009-08-03 11: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