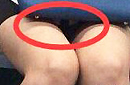在日本,有这样一个特殊群体:他们曾伤天害理却无处悔罪,他们曾杀人放火却缄口不语,他们双手沾满鲜血却不肯认错。随着时光流逝,参加过侵略战争的日本老兵在世的已越来越少,像东史郎那样深刻反省和站出来讲述加害历史、揭露日军当年暴行的更是屈指可数。按照日本二战时的征兵规定,志愿参军者必须年满17岁。所以,即使按照参军与战争结束的1945年来推算,最年轻的日本老兵也已经88岁,很快他们就将与那场战争一起成为历史。然而,历史的记忆注定不会消逝,他们给日本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也像癌细胞一样仍在扩散。
随日本政府推卸战争责任 借国家赔偿领取高额“恩给”
八儿雄三郎,自称今年91岁。这个毕业于日本陆军中野学校,“终战时在大分地区司令部守卫国防”的老兵选择8月15日这个特殊的日子,连同那些美化侵略战争的右翼分子一起参拜靖国神社。“现在,日中关系越来越坏,战争危险也越来越大,如果发生战争,我虽然很想去,但体力已不行了。”八儿雄三郎这样对《环球时报》记者讲。当被问是否愿意让他的儿孙上战场时,这个老人却连连摆手说:“不行啊,不行啊,那样日本就没人了。”
有很多中国人总是在问:“日本人在侵略战争问题上为什么不肯真诚地道歉?”《环球时报》记者采访过一位日本福冈的老兵这样回答:“当年,我们的军队是天皇的军队。宪兵带着征兵令到村里,说你成为‘天皇军队’的一员了。那时我连大阪、东京都没有去过,但我一下子来到中国的杭州,还去了上海、南京。我真的是眼花缭乱啊!一路上,长官告诉我们,这一切都应是日本的、天皇的。你说我能不激动、不兴奋吗?我做梦都没有想到能够为天皇打仗,直到后来我们战败。我也做过许多对不起中国人的事情。但我们的天皇还在皇宫啊!凭什么他没有错,要让我们认错呢!我实话告诉你吧,我做过对不起中国人的事情,我现在就尽量补偿,给到日本的中国留学生提供私人奖学金。但是,在我们天皇没有认错的时候,我也不认错。我们老军人如果都认错了,那不等于天皇也就错了吗?!”在他看来,战后日本的天皇制没有被废黜,应该是日本老兵乃至日本政府不肯承担侵略战争历史罪责的根本原因,而留下这一祸根的,应是美国占领军司令麦克阿瑟。此外,战后日本政府曾经号召国民进行“一亿总忏悔”,意在推卸天皇的战争责任,这也导致老兵们拒绝承认罪责。
战后的日本政府除了推卸战争责任,还给这些老兵及其家属非常优厚的待遇。在这样的背景下,让老兵忏悔和反思变得很难。早在1923年,日本就制定《恩给法》,为征兵发动太平洋侵略战争提供保障,以奖励措施鼓动士兵参战时要冲锋陷阵。日本侵华战争中,在战斗激烈的地区,士兵1年的服役期可以根据“加算年数制度”而被加算为3年。
1946年,驻日盟军总司令部批评日本的军人恩给制度是“世界上最恶劣的制度”,并颁布法令宣布,除重伤病军人外,废止对旧军人或遗属的恩给制度,这导致日本不少旧军人以及战死军人的遗属因经济来源断绝而陷入生活贫困。1947年11月,日本遗族厚生联盟(现“日本遗族会”前身)成立,开始向政府要求国家赔偿。1953年,日本总务省制定发放抚恤金的《援护法》,恩给制度死灰复燃,一直延续到今天。
对仍在世的老兵,日本政府给予每人每月12万日元(1万日元现约合660元人民币)的“退役抚恤金”,每人每月5万日元的“战争补贴”,每人每月3万日元的“恩给”,加起来共约20万日元。此外,日本厚生省每年会向在世老兵支付“厚生年金”,分两次发放,共计35万日元。战后71年来,日本政府还5次以“特别慰问阵亡者家属”的名义,向战死者家属支付特别抚恤金。其中最大的一次是1995年,向将近310万个战死者家庭分别支付高额日元抚恤金,总计达到5238亿日元。
三百个老兵团体仍在滋事
在日本政府的强力保障下,老兵们虽生活无忧,但内心的战争烙印根本无法抹去,有人开始忏悔和谢罪。其中最为人熟知的是参加过南京大屠杀暴行的原日军第十六师团步兵二十联兵队上等兵东史郎。东史郎七次向中国民众谢罪,不顾年岁已高到南京、北京、沈阳、上海等地作证,揭露日军当年的残暴行径,并留下反省历史的《东史郎日记》。 让人遗憾的是,东史郎的行为并未得到日本主流社会的认可,甚至有日本媒体辱骂他“叛徒”“卖国贼”“旧军人的耻辱”“罪该万死”。在日本右翼势力的鼓动下,还有日记中涉及的人物对东史郎提出诉讼。
《环球时报》记者参加过东史郎败诉时举行的记者会见,只见他拿出一份又一份资料,然后愤怒地说,“关于这次审判,问题并不在于原告桥本光治是否杀死一名中国人,他们是想利用这个事件向人们宣称没有发生过南京大屠杀”“法院根本不想看到真实的南京大屠杀事实,也根本没有人想要看到历史,法院的判决是要恐吓为维护历史事实而奋斗的正义人士”。2006年1月3日,想告诉日本人战争真相的东史郎病逝于京都府医院,享年93岁。
在日本学者吉田裕所著《士兵们的战后史》中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日本1945年8月投降时,日本本土有436万名军人,海外有353万人,合计789万人。但在这么庞大的老兵群体中,像东史郎这样在战后站出来揭露战争真相的人屈指可数。对于过去的战争,绝大多数日本老兵选择了沉默!
二战后,在1亿多人的日本社会,近800万老兵有的无声无息,有的蠢蠢欲动。随着1953年日本政府恢复被驻日盟军总司令部禁止的“军人恩给”制度,各种老兵团体先后冒了出来。据《朝日新闻》近日报道,2005年日本还有3625个老兵团体,但目前只有约300个还在开展活动,主要原因是老兵年事已高,在世者日减。
据了解,八成以上的日本老兵团体以曾在同一部队或军舰服役为由头组建。如“南想会”,就是由当年“南进”到东南亚地区的日本陆军装甲车第45大队原队员组成。此外,由军校同学组成的老兵团体占到一成左右。还有以某场共同参加的战役、某个共同生活过的地方为基础成立的老兵团体,如以所罗门群岛战役为纽带的“全国所罗门会”。
绝大多数老兵团体组织活动,一般奉行“只谈现在不讲过去”的原则,尽最大可能避免过去的战争话题。在日本甲级战犯未移入靖国神社后,很多老兵团体仍去参拜。如1955年成立的“日本战友联盟”,以“反共卫国”为宗旨,由发动侵华战争的植田谦吉、冈村宁次等人担任负责人。该组织最多时有30万人,大力推动日本“军备再建”,信条为“让国民广泛理解日本安保问题”“始终站在祭奠英灵的最前端”“尊敬皇室并代代相传”“让国际社会理解日本的立场”。每年参拜靖国神社,祭奠所谓的“英灵”,是该组织最重要的事情。
现在,“日本战友联盟”还定期举办“靖国神社升殿参拜恳谈会”、安保论坛及修改教科书研讨会等,是日本右翼组织的“老前辈”。包括日本《正论》在内的一些右翼杂志,则成为他们“曝光”的平台。
为扩大影响力,日本绝大多数老兵团体从成立开始就拉老兵家属特别是其年轻子女参加。近年来,出生于战后的日本年轻人价值观已发生很大转变,他们更在乎自己的生活,不太关心历史。但这种漠视同样可怕,曾经的那场战争,在他们的印象中更多只是“发生过那么一件事”。由于高龄化和后继无人,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老兵团体相继解散或“活动中止”。2005年,日本“战友会”研究会的调查显示,曾经加入战友联盟的各地战友会,依然存在的不到3成。但正如《环球时报》记者今年“8·15”在靖国神社所见,总有日本老兵穿着旧军服来参拜。
有人感叹:“活到87岁是神对我的惩罚”
有人狡辩:“我父亲在中国付钱买西瓜”
在日本,有的老兵尚有良知,但没有亲身谢罪的勇气。由于忍受不住良心的折磨,有的选择在离世前忏悔。2013年,日本《东京新闻》曾报道过老兵大岛中典在遗书中的忏悔。1937年,大岛中典作为新兵加入日军第9师团富士井部队,在苏州一带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战争结束回到日本后,他总是噩梦缠身。他在遗书中说:“我是个罪孽深重的人,能活到87岁绝不是福祉,而是神对我的惩罚。”他认为“妻子失踪、女儿一家溺水而亡是报应”,这种“家人突然消失的残酷方式”,让他体验到当初自己“给中国人带来的、夺取他们生命和毁灭他们家庭的永恒之痛”。
“我知道那场战争中发生了什么,我也还记得自己在战争中干了什么。原以为时间可以让我内心平静下来,让我逐渐淡忘一切。原来,有些东西是时间都无法磨灭的。几十年来,我一直想把自己的痛苦和经历说出来,让自己好受些。我相信,这样的人还有很多。可是,在日本,在有生之年,我们始终不敢说出来。”2010年9月,一位87岁的日本老兵在家里痛苦地对《环球时报》记者说。采访结束后,这位只讲整个部队活动、没有讲出自己“战争经历”的老兵千叮咛万嘱咐:“不要写出我的名字,即使我死后也不行,因为我还有家人!”2012年,这位老兵带着自己的“秘密”离开了人世。
其实,这些日本老兵对过往侵华战争的认识,也直接影响着他们的后代和更多的日本民众。《环球时报》记者曾去日本广岛旧海军墓地做过采访。那里的一位管理人员吞吞吐吐地说:“我父亲参加1937年‘淞沪之战’,但他常常讲,他们在中国都很守规矩,从老百姓手里买西瓜,都是付钱的。”当时,《环球时报》记者只好对他说:“你父亲真的是辛苦啦!当年,他要跑到中国买西瓜。”听后,他满脸通红,无言以对。
2015年,《环球时报》记者在东京采访参与过“七·七事变”的日本陆军少将今井武夫的儿子今井贞夫。今井贞夫曾在住友工业株式会社工作20年,退休后整理其父遗稿——主线竟然是宣传今井武夫在战争期间从事汪精卫伪国民政府与日本之间的“和平合作”。为此,今井贞夫退休后还去攻读历史学硕士、博士学位。看着他喋喋不休地讲述那段历史,《环球时报》记者质问:“当年,你父亲是不是以武力为前提做‘和平工作’的?”结果今井贞夫沉默了。
2015年9月,《环球时报》记者随日本民间反省侵略战争的“再生的大地”合唱团到沈阳、平顶山、抚顺等地。在列车上,一位日本女士突然对记者说:“我父亲是日本近卫师团的成员,在中国打过仗。晚年,他突然大病,附近寺庙和尚说,‘你家里一定有军刀’。父亲说他用这把军刀杀过中国人。我们把军刀交给寺庙后,父亲的病才好起来。父亲死前对我说过:‘将来有机会,你一定要去一次中国,什么都不用说,就用旅行替我谢罪吧。这次,我就是抱着这个目的来中国的。”
这些事例表明,日本老军人留给后代的战争认识也是不同的。正因为这样,他们的后代对战争的认识也不同,对中国的认识也不同。这种状态,恐怕在日本还要延续相当的时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