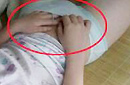如果你想象里的丝绸之路是一幅“驮着丝绸的骆驼商队在尘土飞扬的沙漠中穿行,在中国与罗马之间络绎不绝”的繁忙景象,那么耶鲁大学历史教授芮乐伟 ·韩森(Valerie Hansen)所著《丝绸之路新史》里的“丝绸之路”,肯定会让你惊讶不已。
在这本书里,韩森通过大量惊人的考古发现,彻底改变了世界对这条商路的惯常理解。她试图告诉读者,从来没有一条单一的连续的丝绸之路,有的只是东西方之间的一连串市场:“中国和罗马之间几乎没有直接的贸易活动,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是今天伊朗地区的居民。丝绸并不是这些商路上最重要的商品,中国发明的纸张对欧洲产生了更大的影响,而金属、香料和玻璃与丝绸一样重要。相比之下,这些商路上传播的思想、技术和艺术图案具有更大的意义。”
在出版《丝绸之路新史》之前,作为著名汉学家,韩森著有《开放的帝国:1800 年之前的中国》《传统中国日常生活中的协商:中古契约研究》《变迁之神—南宋时期的民间信仰》等汉学专著。
公元前39年,敦煌以东64公里的悬泉,四名粟特(今撒马尔罕一带)使节向中国官员申诉,说卖的骆驼价钱太低了。在丝路往来的高峰时期,粟特人是中国最重要的外来族群。很多粟特人定居于丝路北道的吐鲁番,从事各种职业,包括农民、客栈老板、兽医、商人等。
四名粟特使节坚称中国官员支付的是又瘦又黄的骆驼价,可他们交付的是更贵的、又白又肥的骆驼。这些粟特使节对市场价格了如指掌,当价格低于预期时,他们对申诉系统有足够的自信。他们还抱怨称,作为持有有效证件的使节,本来觉得自己在丝路的每一站都能得到免费食宿,可到头来还是不得不自掏腰包付饭钱。申诉归申诉,抱怨归抱怨,敦煌官员坚持认为:“粟特人已经得到了合理的报偿。”
这一次纠纷被载入了“文书”。将研究核心聚焦于“文书”,正是韩森有别于其他丝绸之路学者的最大不同。
“这些文书先被遗弃,尔后被偶然发现。其独特性在于它们出自社会各阶层之手,而不仅仅是来自受过教育的富有者和掌权者。这些文书并非有意识的历史作品,也并不指望流传后世。”韩森认为,这些文书常常能为我们展示一个非常鲜活的过去,具有私人性、确凿性、轶闻性和随机性,“没有什么比从垃圾堆中收集到的信息更有价值,因为这些信息从未被篡改过”。
文书里保存着各种各样的细节,展现了一个完整的世界。韩森通过对这些文书的研究,有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发现。她认为,丝绸之路其实是一系列变动不定的小路和无标示的足迹。因为没有明显可见的路,旅人几乎总是需要向导引导,路上遇到障碍就会改变路线。
这些蜿蜒的小路在绿洲城市中交会,途经沿塔克拉玛干沙漠而建的半独立城市国家。其统治者—无论是独立的还是在中国治下的—都会监管贸易、购买货物、提供服务。一旦贸易穿过无人管理的地区进入这些绿洲,就会被高度管控起来。
汉朝和唐朝在中亚驻军时,这种情况显得尤为突出。在唐朝,当中央政府铸造不出与其开销等价的铜钱时,丝绸便有了另一种重要功能。当时的政府承认三种通货:铜钱、谷物和丝绸。因为货币短缺经常发生,而谷物又容易腐烂,因此很多贸易是用成匹的丝绸完成的。很多西北地区的军饷也是丝绸,因此丝绸在西域得以广泛流通。
韩森挑战了人们对这个中亚十字路口的惯常描述。她发现当地居民主要处于维持生计和以物易物的状态,而非从事大规模的长途贸易;她发现在丝绸之路上扮演重要角色的是中国军队,而非商人。士兵在当地市场购物时,丝路贸易便兴盛起来;当国内叛乱威胁到皇帝使他不得不召回军队时,贸易便急剧衰落。
“丝绸之路”这个议题自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在上上个世纪提出后,已有百多年历史。在《丝绸之路新史》中,韩森旅行的顺序分别是楼兰、库车(龟兹)、吐鲁番(高昌)、撒马尔干、长安、敦煌以及于田(于阗)。韩森选择了一个与以往不同的新的切入点:丝绸之路是否如李希霍芬所表示的那样,是一条古已有之的贸易之路?
不存在大规模交易
时代周报:在丝绸之路上交易的主要是哪些人?交易的主要是哪些货品?大规模的贸易是否存在过?
芮乐伟·韩森:丝绸之路上有很多不同类别的商品交易,关键是这些货品的重量一定是轻的。货品越轻越小,就越容易在陆地上运输。所以,丝绸之路用于交易的商品,大概有珍贵的珠宝、石头等,因为它们体积小,一个人携带的量就值很多钱。相反,体积越庞大的、越重的货品,在陆上运输的可能性就越小。我们打捞过很多曾经从事海上贸易的失事船只,船上能够找到陶瓷,这在陆地上就很少见,陶瓷太重,没必要在陆上运输。
至于参加交易商人的具体身份,我们往往不知道。一些文书上会记录人名,其中大部分来自粟特,也有些人来自其他地区,但这些人只是出现在文书上的次数比较多,并不是唯一的贸易者。
丝绸之路上是否存在过大规模的贸易?我在书中也提到了,除了少数例外,文书里面并没有记载任何大型的贸易活动。当然,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理解,就是或许真的存在过,只可惜没有任何痕迹被记录下来。
时代周报:你在书中提出,尽管丝绸之路的贸易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200年,并在公元200年至1000年间进入顶峰时期,但丝绸之路上的居民却从来不知道“丝绸之路”一说。你是怎么得出这个结论的?
芮乐伟·韩森:从目前存留的证据来看,没有当地居民称这条路为“丝绸之路”。或许,他们曾经称之为“丝绸之路”,但现在还没有相关证据证明。我们现有的材料来自在这条路上游历的人,包括很多僧人。我们从这些人的口中得知,这些路最常见的名字是什么,它们从来没有使用过像“丝绸之路”这样广义性的名称,通常会说的是“去往某个城的路”。
时代周报:为什么直到今天,世界仍然对丝绸之路颇为关注?
芮乐伟·韩森:我在耶鲁大学的同事濮德培(Peter Perdue),他的研究方向是新清史,他提过一个说法,即如果中国所有的领土只被汉语为母语的人统治,那么现代中国将会有很大的不同。濮德培的观点这几年一直在被攻击。
现代中国更像一个帝国,有各种不同的人,使用不同的语言,西藏语、维吾尔族语、蒙古语……从这个角度来说,早期人们为什么要去西部、西北部?到底是什么具体的事件导致他们来到西部?他们在那里发生了些什么?又为什么要离开?这些对理解中国的今天和未来的中国都非常重要。
时代周报:具体到你自己,作为耶鲁大学的历史教授,你为什么会对丝绸之路感兴趣?
芮乐伟·韩森:作为历史学家,我一直以来的兴趣都在历史资料方面。具体到中国史,我对任何经过编辑的历史和朝代史都没有兴趣。有意思的是,现在很多人都是围绕着朝代史来做研究的,我却对它们存疑,因为朝代史是被大量编撰过的。
在我的研究领域,很多学者对“士大夫”非常感兴趣,他们非常详细地研究这些文人,与此相比,我喜欢寻找各种不同的出土文书,从中研究普通人的生活。我研究丝绸之路,就是在吐鲁番出土的文书公开出版之后,文书里的内容对我来说很新鲜。从那里面,我可以找到当时人们日常生活的记录,这些记录让我知道了很多中国其他地方没有的东西,这令我兴奋。
时代周报:对出土文书的研究也是《丝绸之路新史》的重点。为什么你的研究这么重视文书?
芮乐伟·韩森:我有一个总体感觉:目前大部分关于丝绸之路的著作,都是有关艺术的,大多讲的是人们抵达了丝绸之路上的各地,见识到了什么新鲜的东西,很少有书告诉读者:与丝绸之路相关的历史文书上到底记录了些什么?这就是我写作本书的初衷。
上世纪90年代中期,吐鲁番有一个研究项目,中美学者都有参与。根据这个项目的发现,可以写出一个基本的吐鲁番史。但是当时我就想,丝绸之路的其他地方、其他遗址又是怎么样的呢?我并不知道要花多长时间才能搞清楚其他地方的历史,但我想到了要根据出土的文书去书写整个丝绸之路的历史。
时代周报:通览文书后,你觉得一般人心中的丝绸之路与文书上记载的有什么不同?
芮乐伟·韩森:在很多人的心里,“丝绸之路”或许是这样一幅景象:一条路,很可能从长安直通罗马,有很多骆驼,骆驼背负着大量形形色色的中国商品……现实不是这样的,但我想这就是历史前进的方式。人们有一个想法,然后历史学家来证明或用证据显示,人们的想象可能不那么准确,然后我们又继续向前探索。
时代周报:书中,你提出了一个主要观点:在“丝绸之路”上,罗马并非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伊朗才是。
芮乐伟·韩森:关键的问题在于,几乎没有证据可以证实存在从长安到罗马这条线路,它纯粹是人们想象出来的。中国与伊朗的贸易,大概从公元500年就开始了。公元400年到500年之间,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可能是印度,总之从来不是罗马。丝绸之路上的商人和商品从哪里来?人们进口了些什么东西?这些资料在文书中都能找到,从来没有东西是从罗马来的。
斯坦因的研究成果仍很重要
时代周报:你怎么评价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针对中亚的考古工作,包括被称为“敦煌盗宝第一人”的斯坦因的成果?
芮乐伟·韩森:要评价他们,就必须参考他们那个时代盛行的标准。斯坦因的贡献非常巨大。即便在今天,如果一个人决定开始研究丝绸之路,他得到的最主要的建议很有可能是“去图书馆读一个月的斯坦因”。只有认识了所有的遗迹、所有的地貌,并且知道斯坦因在不同的地方发现了些什么,才会知道接下来有大量的工作要做。斯坦因的成果仍然是“丝绸之路”学术学习的最基础的部分。
斯坦因生前最出名的事迹,是从中国敦煌带走了成千上万件的档案。他当时装作是佛教的信徒,这样才能拿到文书。如果你读过他自己关于这一欺骗行为的解释,你会发现他其实知道自己向王道士撒了谎。斯坦因当时知道或者说至少大概明白这些文书的价值,他曾经在印度待过,明白原稿在当时的价格。有意思的是,关于自己与王道士协商时的不真诚,他后来都直言不讳。斯坦因的导师是研究梵文手稿的,他学习时很想读读这些手稿,却不被允许。所以,从斯坦因的角度来看,为了得到研究材料,任何行为都是正当的。现在回看这段历史,斯坦因的行为当然不正确,他没有用真挚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诉求或目的。
时代周报:对整个人类发展史而言,丝绸之路有哪些重要贡献?
乐伟·韩森:丝绸之路的主要意义在于:它是不同文化相互接触、碰撞的早期样本。对中国人而言,通过丝绸之路,中国人第一次认识了其他社会,尤其是传播佛教到中国的印度。在学习印度的过程中,中国人更深刻地认识了自己。比如,在读到梵文之前,中国人并没有意识到汉语是全面的语言。当他们看到梵文,就意识到了语言之间的差别。
从世界历史的角度—在我感兴趣的公元200年到1000年这八百年期间—世界的三个文明体,中国、印度和伊朗开始互相接触,同时发展出系统的学习方法和研究其他社会。中国人开始学习梵文,伊朗人开始学习汉语,并且相互翻译。这一切对世界历史的发展很重要,一个已有的文字文明不再孤独,因为另一个同样精妙深刻的社会开始试图了解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