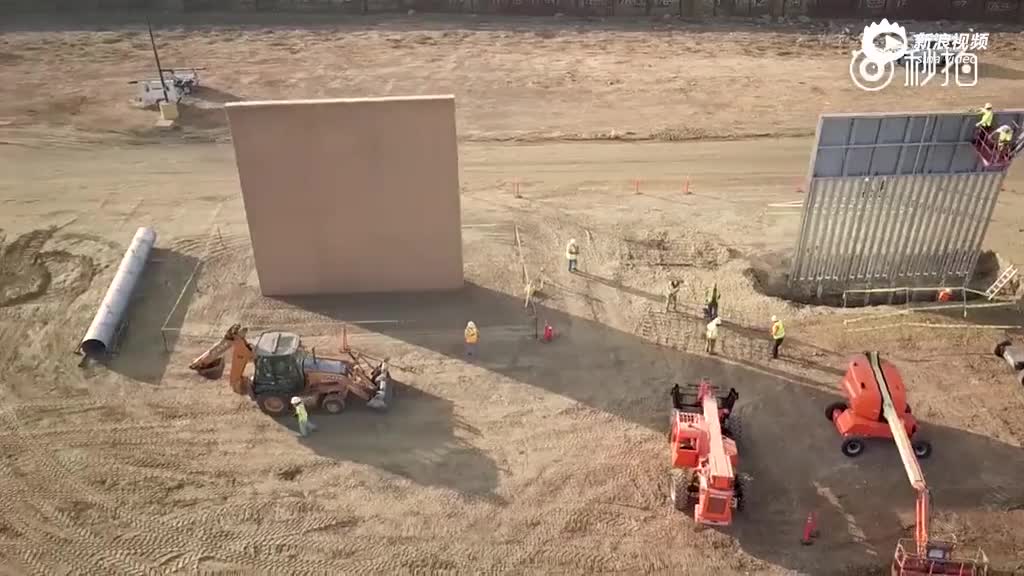文学副刊评论区留言,将综合留言质量和热度,每月评选2位读者,分别赠送名家作品集2册。
阅读是一种心灵的享受。一起阅读,让文学温润的光照亮心灵。

伊丽莎白的礼帽
文 |张楚
好吧,我想讲讲我姨妈的故事。
姨妈风光的晚年生活是从练习书法开始的。她六十四岁那年开始上老年大学。老师是从县职业高中退休的美术老师,他先让他们练小楷,然后练行书,最后是隶、篆、草。教小楷那段时间,大舅生病,姨妈和我老妈轮流看护,一堂课没上;教行书时,姨妈的婆婆病重,姨妈忙前忙后,腿都遛细了;教隶书时,她到哈尔滨帮三姨妈看孙女;等上篆书课,姨妈正好闲来无事。老师说,所谓篆书,就要皆大书而做细笔,劲挺圆润,去肉而筋独存。她听不懂,别的老太太也听不懂,老师又说,小篆长得瘦,性格呢,左不见撇,右不见捺,方中有圆,起止藏锋。姨妈还是没听懂,但她喜欢这些看起来瘦长却肃严的字。她也是瘦得只剩把骨头。她决定好好练篆书。
姨妈退休前是煤炭公司的会计师,做账很有两把刷子。篆书虽然难写,但她充分发挥了一名老会计心思缜密耐性悠长的特点。说实话,那段时间我姨父上官老先生对她颇为不满。姨妈清晨五点就洗手净脸,喝碗豆汁吃根油条,然后急匆匆跑到二楼研墨铺纸,正襟写字。中间连厕所都不舍得去,孙子孙女放学了,她还戴着老花镜一笔一画绣花般临帖。直到下午三点方才蹑手蹑脚地下楼,吃口剩饭冷菜,嘴巴没抹净又溜上阁楼……这样练了一年多,字就比老师的好。老师说,我再给你介绍介绍马先生吧。马先生是桃源县唯一的中国书法协会会员,姨妈随马先生练了两年。这时讨字的就有了,先是亲戚们,外甥外甥女侄子侄女乔迁新居,都要登门求字,装裱后挂在客厅。他们都不知道姨妈写的是什么,反正挂在墙上,黑乎乎挤簇成团,能压得住过往的邪风。再后来就是左邻右舍求字,他们听说姨妈的字好,就拿回去收藏,想着过上数载,没准会卖个好价钱。又过些时日,店铺的老板们也来求字了。他们听县城书届的人说,有年近七旬的老太,写小篆有杨沂孙之风。他们不知道谁是杨沂孙,可他们对这位瘦骨嶙峋、目光犀利的老女人委实充满敬畏。
姨妈后来弃字改行是有缘由的。有次她参加县里的老年书画展,恰巧听到有人评介马先生,就顺嘴说了句:“马先生的字好是好,就是有点懒。”过几日再去马先生家拜访,吃了闭门羹。如此反复几次,马先生仍闭门谢客。过几日让人捎话曰:“疏可走马,密不容针。”姨妈很上火,对姨父说,这些文人墨客啊,口里说的是胸襟,肚里藏的是鸡肠,字写得再好有狗屁用?我活了这么大岁数,没做过亏心事,也不怕别人戳脊梁骨。遂将笔墨送了书友,剩下的几捆宣纸点了炉火。姨父在旁“嘿嘿”笑问,真舍得啊?姨妈撇撇嘴说,有什么舍不得?话虽如此,难免有些黯然,佝偻着腰缩在沙发里看电视。这个时候,是的,这个时候,那个总是拽着威尔士柯基犬出访的英国老女王出来了。

姨妈已经忘记了那次伊丽莎白女王二世代表英国出访哪里。反正,这个世界上最有名的女人穿着身桃红色的套装不停地跟礼兵们握手。对于她这个年岁的女人来讲,这套衣服难免太过艳嫩,但是,她戴了顶同是桃红色的礼帽,却别有风情。这顶礼帽款式古旧,电视里出现外国的贵妇人时,她们总在冬天裹件裘皮大衣,戴顶这样的帽子,手里懒洋洋地端着杯红酒跟男人调情。那天,女王的礼帽轻易将那种轻薄的色彩调配得庄重雅致。“老太太不会穿衣,却会戴帽,”姨妈对正在屋子里练太极拳的姨父说,“我也想买顶这样的帽子。”姨父说:“这么普通的帽子,你自己都能做,还用得着买?”姨妈死死地盯着那个皮肤日渐松弛却总是仪态万方的女王说:“上官啊,你早上喝蜂蜜了?”姨父说:“你什么都要强要好,这点小事还能难倒你?”
姨妈没听出姨父的口吻里全然是嘲讽。这些年来姨父对姨妈的意见越来越大。奔七十的人了,天天练什么破字。以前倒常陪他去河边练拳,如今跟她说话也爱答不理,甚至一整天装聋作哑。姨妈对他来说,简直就是插在稻田里、被夜风吹得越来越丑的稻草人,甚至还不如家里那条时常汪汪乱叫的鹿犬亲。还好,姨父后来迷上了抗日题材的电视剧,每日盯着电视机里的八路军手撕日本鬼子,或两军对垒徒手肉搏厮杀,他就觉得日子还是挺滋润。仿佛家里尚有孩子们在玩过家家的游戏,用不多久,他们就会擦着鼻涕挎着塑料机关枪从某个角落里钻出来。
“明天我去赶集,”姨妈吩咐道,“你陪我一块去。”
“我才不去呢……”姨父嘟囔着说,“你都不陪我看电视……”
“你个没良心的老东西,”姨妈朝姨父抛了个媚眼,“当年你追我时,可替我挑了两年的井水。”
这话在姨父听来,无疑还是很受用的。他们是一个村的。他那时是村里的民兵连长,她是妇联主任。他给她挑了两年水,就去当兵了……姨父连夜将电动车的电充足,又跑到银行取了钱,这才趁早驮着姨妈去赶集。集市可真是好地方。尽管现在县城里每隔三四百米就有超市,可他们还是喜欢熙熙攘攘的集市。只有在集市,他们才感觉到这个世界其实还有很多跟他们一样的人:穿着普通的衣服,说着普通的方言,过着普通的日子,为了一分钱斤斤计较,为了一日三餐灰头土脸。那天在集市上姨妈买了十米布料,买了王麻子剪刀,又买了卷尺和粉笔。在她看来,有了这些家伙什,做出一顶伊丽莎白女王的优雅礼帽完全不在话下。
据姨父说,姨妈在阁楼上鼓捣了两天,终于缝出了她人生中的第一顶礼帽。帽子是常见的玫瑰红,红中夹杂着丝丝缕缕的咖啡灰。这只是顶普通的礼帽而已,不过让姨父惊讶的是,在帽子的后端缀着朵黄玫瑰。姨父揉了揉老花眼,猜想姨妈将一朵花缝在帽子上的手段;再揉揉眼,才察觉那朵玫瑰是用绒布剪的,层层叠叠,肉透明丽,花蕊娇羞地翘着,就差只蜜蜂落在上面了。他盯着姨妈“啧啧”称道:“手艺不错啊!”姨妈说:“那是!也不瞧瞧我是谁。”
那天姨妈双手托着这顶礼帽小跑到我家,要把这顶帽子献给她亲爱的姐姐。可是,那天我老妈正在打麻将。——好吧,我必须说明,麻将是我老妈此生最热爱的娱乐活动。或者说,麻将在她的心里早已经超越了她的儿孙和丈夫。她从服装厂退休后就开始打麻将,麻友是左邻右舍的老街坊。她手艺高妙,每月赢的钱和她的退休金刚好持平。这样麻将不但成为一种娱乐,更成为她敛财的一种方式。为了打麻将她吃过不少苦头。有次她打到子夜两点,回来时老爸睡了,从里面挂了锁,老妈喊了半天老爸也没醒,于是老妈就从两米高的墙头跳了过来。她高中时是县一中的女篮队长,还拿过中学生春季运动会的跳高银牌,可是她忘了,那时她已是七十三岁的老太太……她崴了脚,脚面肿得像馒头。在床上躺了两天,她就迫不及待地拄着新买的拐杖去打麻将了。我和我老爸总算明白,麻将已经是我老妈的氧气,是我老妈的粮食,是我老妈这辈子最难舍的恋人。
姨妈送礼帽那天,老妈的脖子由于颈椎增生,正在家里做牵引:纤细的脖子被固定在一个奇怪的金属支架上,动也不能动,只能眼珠骨碌碌地乱转。即便如此也没能影响她打麻将。老麻友分坐两旁凝神聚气,都期盼借此机会挠回两把。她的孙女,也就是我的女儿偎依在老妈身边,替她摸牌,为她报出每一张麻友发出的牌。姨妈挑门帘进来时,我女儿正拔着尖嗓门喊:“胡爷爷的二饼!”姨妈最烦我妈整天搓麻将。在她看来,这是不务正业的行当。她在旁边默默坐了会儿,我女儿才像太监宣大臣进宫般嚷道:“奶奶!姨奶奶来了!”我妈只是“嗯”了声。女儿又禀告:“奶奶,我姨奶给你送帽子来了!”姨妈也没说话,拿着帽子在老妈眼前转了一圈才说:“姐啊,我自己做的。你瞅着咋样?你是老服装厂的设计师,帮我参谋参谋。”老妈刚才听得老胡抛了张二饼,正在心烦,转着眼珠没好气地说:“什么破帽子!那么黄的一朵花儿,这不喧宾夺主吗?”姨妈没吭声,把礼帽套在老妈头上,前前后后左左右右观瞧一番,这才喏喏道:“确实有些嫩了。”
第二次来我家时,老妈的脖子还在做牵引。姨妈二话没说就将礼帽戴在老妈头上,弓着腰问那些麻友:“怎么样?怎么样?”众麻友赞叹不已,都说,老妹子可真是心灵手巧,干哪行像哪行。姨妈将帽子拿下,在我老妈眼前晃了晃。老妈眼也没睁地说:“好,好,好,确实好。布料好,颜色好,款式好。”
得到了老妈的肯定,姨妈信心倍增,回家连夜赶制了两顶,翌日跑到中心小学门口去卖。第一位顾客是个小学三年级的男生。他看着花花绿绿的礼帽喊道:“真漂亮真漂亮,我要给我奶奶买一个!”姨妈的眼睛都亮了,讨好似的伸着两根手指说:“二十块钱,便宜吧?”孩子就掏了左兜掏右兜,最后连书包都翻了个遍,嘟嘟囔囔说:“哎,只有十七块钱,怎么办呢?”姨妈咬咬槽牙说:“你这么有孝心,奶奶就便宜你三块钱吧。”
没想到的是,姨妈的第二位顾客是她的老房东。姨妈当妇联主任那阵,常跟着公社的领导们四处“蹲点”,当地会为他们找户人家,管吃管住。这个房东正是她在桃源县城“蹲点”时的老相识。她们有小四十年没见过面,两个老太太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惊喜地大声呼唤着彼此的大名,又是握手又是拍肩膀。老房东也是快七十岁的人了,来学校接孙子。姨妈说:“我刚学做帽子,你拿顶戴去吧!”老房东也不客气,挑了顶扣在头上说:“小刘啊,我戴着还真合适。”说完就掏钱。姨妈眼睛有些湿润,说:“我们这么多年的老姐妹,瞧不起我吗?想当年住你们家,攒个鸡蛋你都舍不得给孩子们吃,专门用葱花炒了给我吃。”老房东说:“也好也好,我就不客气了。不过你在这里卖帽子,哪里赶得上去广场卖?那里都是跳舞的,这么时髦的帽子她们肯定都喜欢。”

于是,姨妈的第二战场就转移到广场。这个广场在我们县城里挺有名。有名的原因很简单,县城就这么个广场。早晨拳师们在这里练太极,上午司法局税务局的喜欢在这里搞法律咨询,下午一群干瘪老头在这里甩皮猴写大字。晚上就更喧闹:大妈们和着《最炫民族风》在这里跳群舞,扭着胖屁股甩着大肥腿。她们是这片天地真正的主人,阵容最强大,占据了广场的中心位置。剩下的锻炼者就被挤压到了广场角落:四十多岁的在西北角踢毽子,三十多岁的在东北角打羽毛球,二十来岁的在西南角跳街舞谈恋爱;还有群十几岁的,在东南角玩滑板吃棉花糖滑旱冰。姨妈很快熟悉了地理位置,在大妈们的圈外铺了个地摊,开始卖她的礼帽。
那天晚上,广场舞甫一结束,大妈们立即像苍蝇围住鲜肉般围住了姨妈的帽子摊。她们对姨妈的帽子指指点点,挑这里跳线了那里缝歪了,又不厌其烦地问价压价,把姨妈的耳朵吵得嗡嗡响。这时一老妇人扒拉开人群拿起顶礼帽说:“真精致!多少钱啊?”姨妈说:“二十元。”那妇人惊叫道:“这么贱!这样的帽子超市卖四十块钱呢!我要这顶黑色的!”姨妈定睛一看,这人正是房东,刚要说话,见房东朝她使个眼色,就没吱声。如此开了张,围观的大妈们如得神启般哄抢起来,片刻十来顶帽子就抢光了。待到妇人们散去,姨妈忙将二十元钱归还了房东,说:“多谢老姐姐帮忙。”房东一笑,说:“你以后就来这里卖。都是些没见过世面的人,抠抠搜搜,喜欢便宜货。”
姨妈遇到那些见过世面的人时,已是个把月之后。广场舞因扰民被禁后,这里成了秧歌队的主场。这个秧歌队是县老干部局操办的,队员基本上都是从行政单位退休的女人,从穿着扮相就跟跳广场舞的大妈们明显不是一路。她们也买姨妈的帽子,但从来不讲价钱,只是捏在手里反复观瞧帽子的颜色款式。她们对姨妈帽子上的玫瑰一致赞不绝口,认为这朵玫瑰活色生香,硬是让略显陈旧的款式变得活泼高雅。不过她们的话很少,买了就买了,不会围着她问东问西。姨妈略有些失望,其实她更喜欢听她们多说不相干的闲话,多唠不相干的闲嗑,那样才不像是买卖。不过也无所谓了,她已经卖了九十九顶礼帽,走在大街上看到戴帽子的,就忍不住盯着人家的后脑勺,每当发现了自己做的礼帽时,内心便是那种他乡遇故知的狂喜,恨不得上前揪住人家聊天叙旧。当然,如果恰巧碰到人家戴着她得意的作品,她会有些隐约的失望和愧疚,仿佛是把自己喜欢的孩子贱卖给了陌生人。
秧歌队可能要参加市里的比赛,在广场上练了很久。姨妈坐在帽子摊的后面,盯着她们看。看到有的人笨手笨脚,动作教了五六遍,步子还是迈错,手势还是变形,就感叹人跟人的区别如此大。有天秧歌队排练时,有队员临时有事请假,就空出位来。领队是个五十多岁的妇女,攒着眉头有些不快,唠叨说,腰来腿不来的,就这样还怎么到市里比赛?我看倒不如树倒猢狲散。姨妈跟领队很熟,这个领队面冷心热,帮她卖过四五顶礼帽,姨妈忍不住说:“妹子啊,这秧歌我也会扭,你要是不嫌弃,我就先滥竽充数好了。”
见姨妈这样说,领队也没好意思盘问别的,稻田里缺了棵苗,即便用稗草顶顶,也看得过眼。就说,也好,你就站最末一个位吧,我帮你看着帽子摊。话虽如此说,眼睛却是没离开姨妈。让她吃惊的是,姨妈的秧歌扭起来有板有眼,形神兼备,一抬胳膊一撂腿,一转身一错位,那是分毫不差,那眉眼那派头,一点不比请的教练水平差。两圈下来,领队就拉住姨妈的手问:“大姐啊,秧歌扭这么好,从文化馆退休的吧?”姨妈笑着说:“我哪里有那样的运气?我以前是个会计。”
领队的当然不会知晓,姨妈年轻时在全公社跳舞跳得最好。她们那时跳的是“忠字舞”。手擎红宝书,小心翼翼地踮着脚尖在临时搭建的舞台上飞旋。她那时体态丰腴,不过这丝毫不影响她轻盈迷人的脚步,和那些苗条的姑娘比起来,她的舞步有种乡野女性的笨拙,可正是因为这朴素的笨拙,她的舞步反而衍生出一种奇妙的肉感的美。领队的当然也不会知晓,姨妈那时还编演过一出叫作《积肥员之歌》的舞台剧,曾经参加过县里的文艺汇报演出。姨妈至今还清清楚楚记得里面的歌词:
当个积肥员啊,实在是不简单/要想干得好啊,得先过第一关/第一关是议论关……
“欢迎你加入我们秧歌队,”领队紧紧攥着姨妈的手,“明天我带你到市里买秧歌服。”
这样,姨妈就成了秧歌队里年龄最大的女人。当然,也是秧歌队里的顶梁柱。教练只是一个礼拜来两次,管了东管不了西。姨妈天生是个热心肠,喜欢指点别人。若是换作他人,兴许就会惹出什么不愉快。可姨妈都快七十岁的人了,没人对她挑剔。姨妈练秧歌的时候,她的房东就帮她卖帽子,她的帽子卖得越来越好,秧歌也扭得越来越好。
然而那次秧歌比赛,她们队成绩并不好,有个队员忘了动作,傻傻地在原地站立几秒,仿佛提线木偶断了牵线。最后秧歌队勉强得了纪念奖,还是评委们给了面子。领队觉得脸上挂不住,辛苦一遭,落得如此结果,说话间难免有怨气。没想到队里有人不乐意了,说了些闲话,领队当场就气哭了。姨妈看不下去,“妹子啊,你讲话前可先要拍拍良心!领队训练前挨家挨户打电话,训练完给大家发矿泉水,电话费和水钱都是她自己掏。你们退休前好歹都是有头有脸有知识有文化的人,哪能这样用软刀子扎人?”这才没人言语了。
姨妈也渐渐觉得秧歌队还真是是非之地。那些队员,退休前不是那个局的科长,就是这个局的工会主席,都是人堆里的尖子麦穗上的麦芒。平日里训练,往往为了谁站前位谁站后位,谁是主角谁是配角,谁穿红的谁挂绿的,三言两语就争辩起来。虽一个比一个冷静有礼,慢声细语的,但谁都能听出话里有话,弦外有他意。只是面子上和美团结罢了。姨妈难免心冷,训练排演什么的不如以前积极,抓空就做礼帽。夏天马上到了,这种厚棉线的礼帽戴着热,要换另外的布料和款式。那天做好一顶,刚到了我老妈那儿,就接到了领队的电话。我老妈的颈椎病早好了,可又患了风湿,都快夏天了,还穿着厚棉裤搓麻将。
领队想把工作移交给姨妈,我老妈竖着耳朵听了个明白,撇撇嘴说:“他姨啊,你真是老不舍心。还能活几年?就不能过几天逍遥日子?”
姨妈“哼”了声,从我老妈手里拿过帽子说:“你活你的,我活我的。我们层次不同。”
说实话,姨妈那天的话很大程度上伤害了我老妈的自尊心。虽然我老妈快八十岁了,可是嘴上从来就没服过谁。她望着窗外姨妈的背影说:“你再厉害,当过女篮的队长吗?”
不管怎样,姨妈确实担任了秧歌队的领队。她这个新职位让姨父异常不满。他认为还是继续缝制礼帽最好,既能锻炼小脑,又能赚点小钱,干吗去做费力不讨好的事?七十来岁的人,出那风头会被人笑话。姨妈也觉得姨父的话有些道理。姨父很少说有道理的话。可是既然已经应允了领队,马上撂挑子又有悖姐妹间的情意。
夏天本来就没什么比赛,无非是练练老动作。哪里有开业典礼了,姨妈带着比她年轻的女人们跑场子,每人能赚三斤白糖,或者去乡镇的文化站参加邀请赛,最次也能每人分袋雕牌洗衣粉。队员们本来对这些奖品甚是鄙夷,可是奖品真的拿在手里,那种喜滋滋的感受还是很鲜明。姨妈呢,带了些时日的队伍,也找到些当年的感觉。她年轻时曾在村里组建了“铁姑娘队”。她还记得,1966年的秋夜,她带着一帮姐妹去河边偷偷给生产队的大白菜浇水,一桶接一桶,直到星斗散去,秋衣湿个精透这才回家,累得几天下不了炕;冬天时给孤寡老人缝门帘,村里的陈寡妇晨起发现了棉门帘,以为是神仙怜惜她,跪在地上又磕又拜,惹得她们几个在暗处捂嘴窃笑……那是多少年前的日子?五十年?姨妈觉得,人这辈子,跟活一夏的露蝉,其实没有多大差别。
姨妈从秧歌队里传出绯闻纯粹是因为那个叫徐正国的男人。那时姨妈对卖礼帽已不太上心,房东得了心脏病,不再来帮忙,帽子摊就由几个孩子轮流看管。他们丝毫不上心,看着看着就跑到旁边弹玻璃球去了,弄丢了两顶礼帽。姨妈虽心疼,却也不好多说什么。那天趁中场休息赶紧跑到摊位吆喝两嗓。这时有人走过来低声问价,姨妈抬头报价,见是个男人。两人对望几眼,都忍不住“咦”了一声。男人问,你是周庄的刘姐?姨妈问,你是周庄的铁头?男人笑着说,我都快六十了,你还好意思叫我的小名?姨妈说,那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按庄户人家的辈分,你还得管我叫姑姑。男人嘿嘿笑了。这个小名叫铁头的男人姨妈再熟悉不过,从小聪慧,不过因出身富农,早早辍了学。等到恢复高考,他考上了粮校,毕业分配到粮局,后来下岗,再后来开出租车,一直没孩子,听说他老婆前几年得癌症死了。
姨妈说:“要是喜欢就拿一顶。谁戴啊?”
徐正国说:“能买给谁呢?我妈呗。”
姨妈愣了一下说:“呦,我嫂子还健在?”
徐正国皱着浓眉说:“唉,我是屎壳郎的命。老婆死了,守着老妈混吃等死。”
姨妈沉默了良久才问:“我嫂子……还好?”
徐正国点支烟说:“小脑萎缩加脑梗死,跟植物人似的。就剩下那口气,死活都不肯散。”
姨妈叹息一声,说:“我多少年没见过嫂子了。”
那天晚上姨妈回到家里,径直进了卧室躺上床。她很想跟姨父聊聊天说说话,可姨父正在看一部关于“二战”的纪录片,吆喝了几嗓子都没有吭声。姨妈突然就有些伤怀。姨父是出了名的炮筒,脾气暴,无论是跟同事还是跟亲戚朋友都如此,因此一生得罪了不少人。这么些年来如若不是姨妈暗地里说软绵话,不晓得往来的还能有多少人?不过姨父对姨妈向来言听计从。他怕她,他知道,如若不装出怕她的模样,她就会不停地讲道理,也许日子一辈子都不消停。那天他没有跟姨妈搭腔,因为忘记了温牛奶,他以为姨妈肯定会给他上一堂关于牛奶的营养课。
第二天晚上,姨妈在广场上又遇到了徐正国。徐正国牵着只小狗。那是条又脏又丑的巴儿狗。他站在姨妈的帽子摊前晃来晃去。姨妈问:“我嫂子怎样了?吃东西了没?”徐正国就说:“还是老样子,喂她什么就吃什么,如果哪天把狗屎塞进她嘴里,她也会嚼得津津有味。”姨妈唉声叹气道:“你呀,要对你妈好才是,你都不知道你妈怀着你时遭了多少罪……”徐正国“嘿嘿”地笑了两声说:“我倒是希望她当初没将我生出来呢。”

那天晚上,秧歌队的队员看到姨妈和那个男人聊了很久。她们不知道两个人在聊什么,但是她们认为两个人聊得很投机。姨妈不停地小声窃笑,而那个精壮的男人颠晃着脚抽着烟,还时不时用手抚摸一下那只烂了眼睛的小狗。队员就走过去提醒说:“刘大姐啊,该走场子了。”姨妈说:“你们先练着,我碰到了老乡。”
第三天晚上,姨妈跟这个所谓的老乡又聊了很久。姨妈甚至忘记了卖帽子的事。秧歌队的队员们就觉得事情有些蹊跷。她们中的一个神神秘秘地提示大家,是不是姨妈老来要红杏出墙呢?她提出这个话题时大家都禁不住倒吸口冷气,忍不住将目光甩向姨妈和徐正国。姨妈的嘴唇一直翕动,而那个徐正国摆出副侧耳倾听的样子,时不时地点下头,然后目光热烈而持久地注视着姨妈,仿佛姨妈不是个年近七旬的老太太,而是某个当红的女明星。“确实有点问题,”有个人说,“你们忘记了李米香的事吗?”队员们恍然大悟般颔首不止。丧夫的李米香是个八十二岁的老太,膝下儿女成群,对她孝顺有加,怎么就被个六十八的男人(据说是从评剧团退休的小生)迷得神魂颠倒,要跟男人领结婚证,还要把房产证改成男人的名字。更让人难以启齿的是,她住院期间还当着病友的面跟老男人亲嘴,她可是戴着副假牙呢……
队员们都觉得问题有点严重。她们觉得,姨妈是个很好的领队,为了挽救领队的名誉,她们必须做点事情。如果事情真如她们猜度的那样,该如何轻描淡写又不伤和气地处理这件事情?这时有个队员涨红着脸大声说:“我想起来了!刘姐有个亲姐,跟我婆婆是牌友。我把这事跟她姐姐汇报一下,让她提醒一下刘姐。我们毕竟是外人,人家毕竟是亲姐妹。”队员们对她的建议颇为认可,夸赞她头脑灵活。
这样,我老妈就知晓了此事。对于这桩桃色新闻,我老妈认为根本是扯淡。她哼哼着说:“她们根本不了解你姨妈!就是搞婚外恋,她也看不上徐正国。她眼光可高着呢。当年,有多少工人、士兵和国家干部追求她?”本来她想亲自找姨妈谈谈心,可她确实比奥巴马都忙。那些牌友眼巴巴地瞅着她,怎能忍心三缺一?于是她把我拎过去。
她拎我是因为我是警察。虽然她认为让一个当警察的外甥去调查姨妈的婚外情不是件体面的事,但总比将来闹得满城风雨要好得多。她最后叮咛我说:“儿子啊,这件事最好的解决方式就是打草惊蛇。你学的是刑侦,干的是刑侦,还用我教你吗?有问题及时向我汇报。我手机二十四小时开机。”
老妈接到线人的电话是第五天晚上。线人说,那男人又来了,姨妈跟他又聊了半天,后来跟副领队匆忙打个招呼,就背着书包跟男人走了。我老妈在电话里对我嚷道:“不管你在哪儿,立刻给我去看看!我既然把你姨妈嫁给了你上官姨父,就要对他负责到底!……和了!”
作为姨妈最亲近的外甥,多年来我已经把她当成了亲妈:我结婚前老加班,姨妈给我做蛋炒饭时,我老妈在打麻将;我结婚时,姨妈戴着花镜给我做新婚的被褥,而我老妈在打麻将;前几年冬天冷得异常,姨妈给我缝制厚厚的棉裤时,我老妈在打麻将……我觉得我比老妈更有义务维护姨妈的名声。
当我蹲伏在徐正国家那条破巷子的垃圾箱里时,曾做了半天思想斗争。我做斗争首先是觉得这件事情很滑稽,如果被姨妈知道我在跟踪她,她会如何想?其次是那个庞大的垃圾箱臭极了,我担心用不了多久我就会变成一只青头苍蝇。还好,很快我就听到了姨妈的说话声。她这个人最大的缺点就是说话声音过高,仿佛真理总是掌握在她手里,她必须用更磅礴的肺活量将那些真理传递给他人。徐正国一直没吭声,只是掏钥匙开门。当他们进了庭院后我如大赦般从垃圾箱里爬出来。徐正国没有从里面锁门,我很轻易就闪了进去。他们开了灯,从窗外往里看,炕上侧坐着个老得看不出年龄的女人。
窗子开着,我伏在窗户底下听姨妈说:“嫂子啊!还认得我吗?”
那个老太太仍然坐着,没有半点声息。姨妈又说:“嫂子啊!我是老丫头啊!”她的声音有些颤抖,“我三十多年没见过你了!我跟上官随军,转业,到煤炭公司上班,退休……过得多快!没想到你跟侄子住在这儿……”
徐正国嗫嚅着说:“你说什么她都听不到。她就是个傻子。傻子还知道拉屎拉尿呢。”
姨妈没搭徐正国的腔。“我今天来看你,也是思前想后才来……”她注视着老女人,嘴唇嚅动良久才慢吞吞地说,“那天见到铁头,就想起了一件事。这件事在我心里压了多年……”她抬起胳膊拢了拢老人凌乱的白发,“还记得吗?一九七一年,革委会批斗你,曾抄过你的家。”
徐正国歪头瞥了一眼姨妈,姨妈就对他说:“你那时也就十多岁。”
徐正国说:“谁说我小?我可记得你在舞台上跳‘忠字舞’。为了看你跳舞,还被村里的狗崽子揍个半死。他们都骂我是‘黑五类’。”
姨妈没搭理他,继续盯着老太太说:“抄完家,革委会的又要押着你到街上游行。”
徐正国嬉笑着说:“游行就游行了,谁让她嫁给了地主呢。”
姨妈扭头对他说:“游行之前,他们要给你妈理‘阴阳头’。”
徐正国说:“理就理吧,谁让她嫁给了地主呢……”
姨妈沉默了半晌才说:“是我理的……”
徐正国瞄姨妈一眼说:“我一点都不记得了……”
姨妈说:“我爹妈死得早,姐姐们又都出了嫁,我从十五岁就当家立户。嫂子可怜我,过年过节总忘不了给我买点好吃的……你们家那时过得也不易。”
徐正国说:“那倒没错,我记得有年腊月二十三,她还让我给你送过一斤猪肉。”
姨妈再次沉默了,只是用手抚摸着老太太的头发。我想她一定很难过,用不了多久她也许就会哭出声来。我从来没有见姨妈哭过。
“我给她剃‘阴阳头’时,她就那么安静地坐着,连动都没有动,仿佛我是理发店的高级理发师……她的头发又黑又密,一绺一绺掉地上,又被风吹到了灶台边。她不知道,其实我的手一直在打战,那把生锈的推子时不时就夹住了她的头发,她也没喊疼……其实理到一半的时候我差点就撒腿跑了……她右边的头发被剃光了,露出青白色的头皮,而她左边的头发硬扎扎地支棱着像堆茅草。我听到她问,理完了吗,老丫头?她管我叫老丫头,多年来她一直管我叫老丫头……她的声音很平静,一点没有抱怨的意思。我支支吾吾地说,马上就好了。这个时候,她突然侧头瞥了我一眼……”姨妈就是这时哭起来的。我们都知道,老人们哭泣的时候是没有声音的,可我知道姨妈哭了,“她就那么着看了我一眼……我这辈子都忘不了……她说,老丫头,先让我照照镜子……”
姨妈弯腰抱住了木乃伊般的老太太,嘴里嘟囔道:“‘文革’结束后,你再也没瞅过我一眼,再也没跟我说过一句话,我知道你心里恨我……说实话,我一直想给你赔不是……”
可能是终于把话说出来,姨妈看上去轻松不少。我看到她窸窸窣窣地从背包里拽出顶蓬松的粉红色礼帽,抻了抻帽檐,郑重地戴到老人头上,又后退两步端详半天,这才说:“这顶帽子啊,我就送给嫂子了。尽管你不会说话,不过,我知道你肯定喜欢。”
姨妈没等徐正国再说别的,径自转身出了屋子。我听到徐正国犹豫着问道:“你就这样走了?不待会儿了?”
姨妈说:“有什么好待的。我要是不早点回家,你姑父肯定又忘了温牛奶。”
好吧,这就是我姨妈的故事。当然,也许根本谈不上是什么故事。我还记得姨妈从屋子里大步走出来,徐正国也没有送客。我就蹑手蹑脚地跟在姨妈身后一直前行。姨妈是越来越瘦了,走起路来悄无声息。月光下她的背有些佝偻,我记得我的姨父上官先生曾经说过,姨妈越来越像一个插在稻田里的老稻草人。说实话,像我姨父这样的粗人能想出这样的句子,还真是不容易呢。
本文来自当代微信公众号

张楚,一九七四年生,唐山人。作品散见于《人民文学》《收获》《十月》《上海文学》等刊。著有中短篇小说集《樱桃记》《七根孔雀羽毛》《夜是怎样黑下来的》。曾获“大红鹰文学奖”“人民文学奖”“林斤澜短篇小说奖”“河北省文艺振兴奖”“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奖”“《十月》青年作家奖”。二〇一一年入选“未来文学大家TOP20”。被《人民文学》和《南方文坛》评为二〇一二年“年度青年作家”。第六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

更多猛料!欢迎扫描左方二维码关注新浪军事官方微信(sinamilnews)
推荐新闻
- 【 新闻 】 俄媒称这项重要资源正从美流向中国
- 【 军事 】 出鞘:美英法空袭叙利亚对中国的启示
- 【 财经 】 内蒙古网站早前发文 专家力挺鸿茅药酒
- 【 体育 】 亚冠-广州恒大3-1胜出线 申花0-0平悉...
- 【 娱乐 】 网曝霍启刚郭晶晶泰国度假享受二人世...
- 【 科技 】 社交平台拉新的标配是小游戏?
- 【 教育 】 花巨资上“止吼课” 家长们还是太焦虑...
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电话:010-62675637
举报邮箱:jubao@vip.sina.com
Copyright © 1996-2017 SINA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新浪公司 版权所有